ע��ʱ��2012-5-27
��� ö
����
|
|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ʫ�� ���ߣ�ӽ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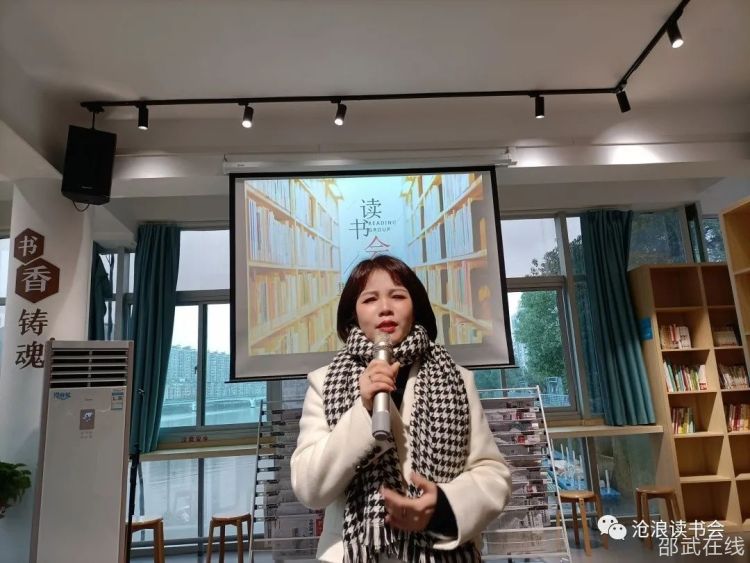
�ڡ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Ե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һƶ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ɢ�Ŀ��Կ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ȵ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Եġ��Ȿɢ�ļ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ƽ���ⲿɢ�ļ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ڴ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졢���ء����̷����硢��Ȧ����ҩ̯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ͼ�¼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ξ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̬�ȣ��Լ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ͨ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ȡ�
���ⲿɢ�ļ��У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ϵ�Ͷ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ñ����¶ȵĴ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ũ�����ĸ�֪��
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ijһʱ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˵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ۣ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˴˲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ũ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ɷָ��һ���֣����DZ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Ƶĵ��ȣ��ջ��±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Ի�á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ܿ��ţ��㿴�ҵ�ĸ�״Ӳ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ͷ����ľͰ�����﹡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δлĻ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ˮ�Σ���Ԥʾ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;ͽ���ʼ���ǵģ�ʢ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ͥ��ů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ͺͼ�ͥ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˸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ӡ���д���硱��һƬ��Ұ��ֻ�м����ڴ�Խ��һƬ��Ұ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Ż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ʫ�⣡����д�ˡ��硱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С��硱����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з��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ף��Ǵ�ׯ�Ľ����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ߡ���д����𡱣��ԣ�����ǻζ����鷿���㿴���ǵ��Ź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ҡ�εĿ��ӣ��Dz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ζ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ǡ��ζ����鷿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ջ�
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ı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г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˺�ũ�����ֵܣ���ս�ѣ����DZ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³��ֵĸ��ס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ʵ�ڵģ��г��صļ��䣬Ҳ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Ĭ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ˡ��ơ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磬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ƣ��ͽ��ꡣ
���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ϡ����Դ���Ȼ����Щ��ͨ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еĹػ�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Եġ������˸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߶Գ����䱰�����Ĺ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ˣ��и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һ����ׯӦ����һЩʳ���һЩ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ֲ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г�ˣ��ల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һ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ΪС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˵ı����黳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Ӧ�ú����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ȵģ�ֻ�в�ɱ¾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ܹ�Ϊ�Լ��ṩ���õ����滷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ܷ���С���е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졢һͷ�ܼ�����֭����ţ��һ�쵽���ϲ�£�۵Ĺ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æ��֯����֩�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ӡ����Щ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úͻ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塰Ҳ�����ܵ�֯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⣬���иж����ǵĻ��У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ƫԶ�Ĵ�ׯ����ʹ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Ҳû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ȺͿ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˵�Ԫ�ء���ƽ���Լ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Ƚ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κ�ʱ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
�ڴ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ÿ���ֶ��飬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벢û�б���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д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÷ḻ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һ���˵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˺ܶ���ҩ�����ѡ�ͬѧ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о��Լ��Ŷ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˾ܾ����˿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а˾Ų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��ڲ���ϵ��ˣ�һ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ֻ���ڸ���һЩ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˻��ŵļ��ѺͰ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Ȼ��ǿ�ػ��ţ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ֲ��һ����
ÿһ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滺�ģ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ͨ�ģ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˶��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صġ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
���ڣ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˵���굽�˺�Զ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ȥ�˺�Զ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磬�Լ���Щ�ڹ����ʵ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ػ��ŵ����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/���

Ϊ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й���Э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ӵ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ȴӢ�����Ŷ�̾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µ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鹹��ɢ�ļ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
��Щ����ͨͨ��ũ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ׯ�ĸ첲���ȣ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Dz��Dz�ʵ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˶����û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ͻ�Դ�ׯ����Ѹ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Խ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ס���һ��Ѱ��ũ�ҵ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Ⱦ�˶Թ�ȥ�ں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º͵��˲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ɸУ�һ��ϸ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IJŻ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ʫ�ˣ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ն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˵Ļ�������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ģ��ڴ�ذ���ȥʱ���ڴ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ĽŲ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ﲻע��ʱ�����칬��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Ҫ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𣿼Ҿ��أ�����ʲôҲû��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ǵ�һ�ģ����ǿ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ʣ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һ�ξ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Ա���õص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̴��Ǵ�ׯ�Ļ��롣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ġ���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ѭ���У����仯�ţ��ֲ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ʵʵ��̻¶������һ�У����Ǵ�˾�ռ��ߣ�����ʫ�˵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ܳ�����ʫ�黭�⣬���ܲ����ر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롣��ƽ���е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֮��̾��Ϊ֮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أ���Щ��Ȥ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Եġ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Ϊ���ߵ���ǡ���˼���۷���ѧ����ȥƷ����Ȼ��Ȥζ��ѧ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С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˵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峤�����ij��ӣ��ع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С�ǹ¶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˵Ŷ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롣���ٸ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ڤ˼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ѵ����и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С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ֱ�����־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ɢҶ�������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죬�ҳ�����ֽ��ͻ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ִ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ᶨ�ߣ�һ����ס��į�ߣ�һ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Ȼ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ܵ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վ����ǰ�Ŀյ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ո����Ѹ�ٵسԵ�һƬ��ơ���Щ����ڽ��֮�е������أ�һ�ѱ��¹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ؼ�֤�����Ĵ��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ž�����Ҷ��һ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ϼҷ��ӡ���ҩ̯�������硱����ĬĬ�ػر��š�ĸ���ǰ��ٲ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Ρ�ʯĥ�Ρ���ϯ���Ρ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һ���ܽ����뻯Ϊ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ͬ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ϵ�أ��첻��Ϥ��Ҳ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ͺ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ʶ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˼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Ϊ��ƽ���֣�
|
|